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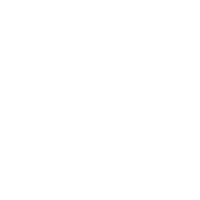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的失败和湘鄂边中心县委在崇阳的建立(四)
“六七月事变”及湘鄂赣省委机关的突围
1934年1月,设在江西万载小源的中共湘鄂赣省委机关被敌占驻,省委机关转移到铜鼓幽居、祖庄一带。次月,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率领省委机关、省保卫大队及赣北独立团,从幽居出发向西行进;5月上旬到达崇阳大沙坪时,遭国民党三十三师冯兴贤部的秦、张两团夹击,阵亡300余人。省委机关折向东行,同月到达修水、画坪。红十六师在浏阳坳与红十七师分别后,转战到了修河(水)西岸的全丰、画坪一带。
此时,敌五十师、三十三师、二十六师及驻修水的吴抚夷保安团一齐扑向修河(水)西岸,包围全丰、画坪。为了摆脱敌人,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:“先向鄂东南方向突围,以后再折回修水、铜鼓、宜丰、奉新边去”①。在红十六师的掩护下,省级机关安全转移到了鄂东南,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在画坪同敌激战中,遭受了严重的损失。
“省级机关到鄂东南后,红十六师四十六、四十八团也全部到达鄂东南,不久与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会合。由于师长高咏生牺牲,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受损,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决定对红十六师整编,由徐彦刚兼任师长,陈寿昌兼任师政治委员②。”红十六师整编后,又在鄂东南扩充了一批干部和地方武装,共计2000余人,同省级机关一道向南行动。在武宁澧溪击溃敌人1个营,渡过修河(水)到达洞口。这时,敌二十六师已从后面追赶上来。陈寿昌主持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在洞口阻击敌人。由于对敌人的兵力作了错误估计,把敌两个团误作1个团,加上我军对地形不熟,激战1天,不但没有击退敌人,红十六师反伤亡数百人,部队撤出战斗,向修铜宜奉边龙门山区转移。
1934年6月,湘鄂赣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转移到龙门山区奉新的百丈、西塔,计划在这一带驻扎下来,建立根据地。省委派出一部分干部深入乡村,帮助发展基层党组织,建立苏维埃政权,并决定在百丈召开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,各地出席会议的代表先后到达百丈。这时,敌五十师、七十七师、十八师和六十二师数倍于我的兵力向省委机关驻地包围过来,形势十分危急。省委命令撤离百丈、西塔,向平江黄金洞转移,并将各地前来参会的代表编成特务团,随同省级机关行动。此时,敌人已形成对我军的合围,省委和红十六师迅速组织突围行动。由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四十六、四十八团向靖安、永修方向突围;由陈寿昌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率领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及省直机关干部、党代会代表组成的特务团向宜丰、铜鼓方向突围。结果,徐彦刚所率的四十六、四十八团突围至斜岭遭敌十九师夹击,损失惨重;陈寿昌所率的四十七团和省直机关干部行至宜丰高视时,遭到敌五十师第三〇〇团伏击,伤亡严重,突围未成。
为了保存有生力量,陈寿昌率领的部队分三路突围:一路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何振吾率领,从西南方向向黄岗口、排埠突围;一路由省政治保卫局代局长邓洪率领,从北方向向铜鼓三都、西向突围;一路由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手枪队,保护双脚溃烂行走困难的陈寿昌从北面突围。结果,何振吾率领的队伍在突围时被打垮;邓洪率领的一路主力被打散,几天后收集被冲散的部分人员回黄金洞;刘玉堂带领的手枪队,因手枪射程不远,无法突围,只好返回宜丰的山里隐蔽,一个星期后,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,回到黄金洞苏区。
徐彦刚率领的一部自斜岭战斗后,红十六师四十六、四十八团只剩下三四百人,几经艰难曲折,转移到永修云居山。这时,敌人又从四面包围过来。徐彦刚在云居山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将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,突围后能返回黄金洞就返回黄金洞,无法回黄金洞的就到第二作战分区,或者到华林寨山区开辟新苏区。突围小队分编后,迅速向四面突围。由于敌众我寡,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,少数突围出去后,一部分回到黄金洞,一部分到了华林寨山区。徐彦刚带领十几个战士杀出重围,历尽艰险,返回黄金洞。
这次突围战斗中,省直机关干部和红十六师指战员奋不顾身,英勇战斗。许多人血洒青山,骨抛原野,为湘鄂赣苏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谱写了湘鄂赣苏区斗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。当时,红十六师和省直机关干部、党代会代表共2000余人,大部壮烈牺牲,一部分失散,部队“仅剩约一营人”③。全省累计损失枪支4000余支,牺牲1万人左右。此后,湘鄂赣“苏区受到敌人蹂躏、摧残,分成为11块,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,横直二三十里,小块只有几里宽。④”湘鄂赣省委与中共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联系中断。因这次惨痛的失败发生在六七月,当时中共湘鄂赣省委称为“六七月事变”。“六七月事变”导致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失败,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提前3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。
①《湘鄂赣苏区史稿》,第228页。
②《湘鄂赣苏区史稿》,第228页。
③《徐彦刚、傅秋涛给任弼时、肖克转中央军委的报告》,1935年6月7日,《鄂南党史文献资料》第2辑,第759页。
④《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的信》,1935年6月30日,《鄂南党史文献资料》第2辑,第767页。
